前幾天,我的一位朋友在群聊里分享了李誕的一段脫口秀,幾秒后,就有另一位朋友在群里回復道:“又是李誕,抱歉,我現在是李誕PTSD。”
兩人在群里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辯起來,我默默地看著他們的言辭從冷嘲熱諷到簡單粗暴,最后,爭吵以發視頻那位朋友的一句話終結:“別再PTSD了,我都PTSDPTSD了。”
 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所以什么是 PTSD?PTSD 的全稱為 Post‐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,創傷后應激障礙。它是個體在遭遇重大精神創傷后留下的后遺癥,患有這種癥候的人群大多擁有一段相當殘酷的經歷,例如目擊重大死亡事故、親歷戰爭或恐怖襲擊等,事后,這段經歷就成為了他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夢魘,時刻侵擾著他們的生活。
直到后來有人把它移植到網絡世界,它的意義也徹底改變。
最開始害網友們大面積患上“PTSD”的是吳京和他的《戰狼2》。作為 2017 年現象級國產電影,《戰狼2》一經上映就贏得了極高的口碑,至今依舊以 56 億這個數字雄踞內地電影票房之首。在電影上映的當時,許多網友在豆瓣和微博為它拉粉造勢,信息壁壘被無情打碎,網絡上鋪天蓋地盡是對《戰狼2》的褒獎和贊美。
當然,再好的電影也不可能博取所有影迷的愛。《戰狼2》這股風潮在愛狼之人的助推下幾近演化為一場狂歡時,對《戰狼2》不感興趣的人,反感這種粉絲狂熱的人,以及對流行冷感的人慢慢發現,原本應該屬于自己的網絡空間中也被與《戰狼2》有關的內容入侵了。
盡管不想看見與戰狼有關的內容,但刷到哪都能看見戰狼,于是,他們開始患上“戰狼PTSD”。
在“戰狼PTSD”這個詞被創造出來后,愛狼之人與厭狼之人之間的愛恨情仇已經不在我感興趣的范圍內了。我感興趣的是這個詞匯本身,在“戰狼PTSD”出現后,“PTSD”很快地成為了一個輕巧的標簽,取代了粉絲和黑子,被廣大網民隨處張貼。
但事實上,“PTSD”這個標簽比單純的“粉”和“黑”更加復雜。對于貼上了“戰狼PTSD”的人而言,他們并非全是黑戰狼的噴子。在我有限地觀察和體會中,“PTSD”這種表達更加模糊。它占據了喜好程度光譜上相當寬闊的一段地帶:冷感、反感、厭惡直至痛恨,都被囊括其中。有些“PTSD”患者會在網絡上發出惡毒的人身詛咒,而有些人只是在說:“它好不好與我無關,我只不過是單純地對它不感興趣”。
這種高度概括的詞匯充滿被濫用的嫌疑,當然,也得益于存在一片讓它開枝散葉的土壤。
互聯網世界的廣闊和狹小在此刻矛盾地交疊在了一起。說它廣闊,是因為在網絡上你永遠可以找到你感興趣的事物,狹小則在于,每個人似乎都在逐漸失去一片專屬于自己的網絡空間。
“PTSD”的出現,就是因為這種狹小。當一個新事物在網上火起來后,相關的信息就會像火山噴發般涌出,讓所有人都難以逃避。在一個相互聯結的網絡中,這些海量信息滲入的方向往往就失去控制。“抖音PTSD”、“快手PTSD”、“直播PTSD”接連登場,就是因為原本不玩抖音的人難以逃過神曲的侵擾,不玩快手的人還是會聽到那聲震耳欲聾的“奧力給”,不看直播的人也最終學會了主播們的口頭禪。
互聯網的算法是不在意質量的,它只是單純地依照受關注的程度對所有信息進行排序。而當營銷成為社交網絡的一部分,內容的大面積傳播就成為可以被預測并且被準確實現的事件。每一個娛樂熱點背后都有資本的影子,而網絡上的人,在整個傳播鏈條當中也不過只是一個數字。
即便你苦心經營自己的網絡社交圈,也依舊無法躲開一些觀光團和粉絲團。而在虛擬世界中,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和相處更多地依賴于文字,這種相處模式讓人無法感受到個體的實實在在,相處中的邊界感也就隨之被消除。
于是就像在賽博朋克電影里,出沒于午夜時分的飛車黨攪動著城市的安寧,刷熱度的不速之客們在互聯網世界神出鬼沒。他們也不會計較這些言論給他人帶來的困擾,肆無忌憚地順著網絡四處流竄,留下數字版“到此一游”便揚長而去。
這似乎又會通向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:當現代人如愿以償得到了海量的信息,作為交換,也失去了過濾和挑選的權力。
未來到來的速度從不體諒人類行進的步調。短短十年內,手機就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,即便局促一隅,點點屏幕就能召喚快遞小哥將需求送上門來,不必出門就能了解世界各地正在發生什么,各式各樣的生活體驗被總結、被展示,被投喂給屏幕前的每一個人。技術換代的周期逼迫人們追趕著適應,21 世紀初人們對“信息高速公路”的欣喜尚歷歷在目,一個轉身,每個人都已經被信息擠壓得喘不過氣來。
“PTSD”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一種微型反抗,亮出這層身份的人就像一只領地即將被侵占的響尾蛇,豎起沙沙作響的尾巴對周遭發出勿擾信號。
話說回來,單純地解讀身份標簽,并用「受害者」或「裝逼」的二元分法來對號入座總是容易的,但也是淺薄的。這些年來,互聯網上冒出來的網絡病并不算少,一開始,因為手機上的通知小紅點不點掉就不舒服,許多人都以“強迫癥”自居;后來社交網絡如毛細血管般地深入,把社交壓力傳導到生活的每個角落中,于是有了“孤獨患者”和“社恐”;而現在,則輪到了“PTSD”。
這些網絡病在互聯網上標簽化,喜歡在網絡上展現自我的年輕人們一擁而上,爭搶著把它們貼在自己身上。久而久之,它們變成了一種常態。人們習慣了手機里永遠有消不完的紅點,習慣了社交壓力的精神負擔,也習慣了海量信息下的無可逃避。
網絡病的標簽之下,是每個試圖抵抗時代浪潮的人曾經搏擊的傷痕,但最終他們依舊抵不過浪潮湍急,被推著往未來走去。對于這些標簽,你當然可以說人們用標簽標榜自己,并依賴它尋求某種群體身份,也可以說它是跟風,是一種矯揉造作的無病呻吟,只不過這是放在任何標簽上都成立的陳詞濫調。
而無論這些標簽有多么輕浮,它底下依舊埋藏著某種真實。“強迫癥”面對永遠點不完的紅點時的苦惱是真實的;“社恐”在面對社交時的忸怩和糾結是真實的;“PTSD”被各種自己不感興趣的信息轟炸后的煩躁也是真實的。在這些場景中,標簽成為一層無可奈何的鎧甲,每一個用“強迫癥”、“社恐”或者“PTSD”武裝自己的人,都在試圖用它們表達自己的微小抗議。
只不過它們最終還是會變成玩笑,被消解為一個梗,然后匯入信息流里,被推送到屏幕上,變成一個新的話題,在這種循環中,抵抗最終變成了助推的力量。
而“PTSD”,也從一種無力的抵抗,變成了一種抵抗的無力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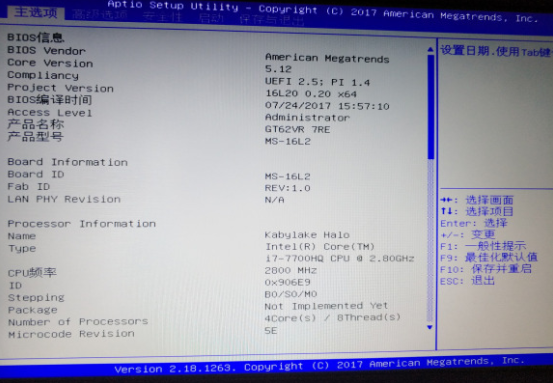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
營業執照公示信息